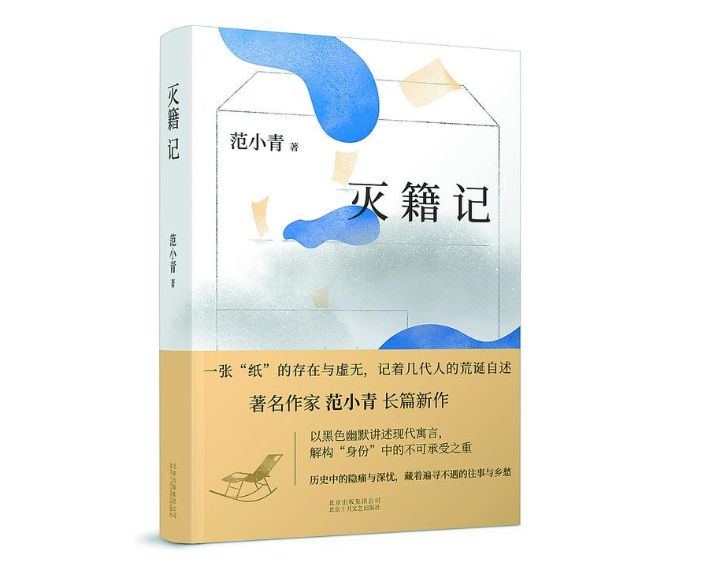《滅籍記》》是范小青長篇新作��,2018年12月出版�����,一經(jīng)問世�,好評(píng)如潮����,入選多個(gè)重要文學(xué)排行榜��。關(guān)于這部作品的信息�,更是占據(jù)搜狗搜索5個(gè)以上頁碼�。時(shí)隔數(shù)月后�����,我再來寫��,簡直連應(yīng)景都算不上�����。但是自讀完《滅籍記》后�,我一直心心念念無以了卻。
先告白一下����,我是范小青的忠實(shí)粉絲,她出版的作品我?guī)缀醵甲x過。
有一件事我一直沒和她說�����,估計(jì)她也不會(huì)記得����。那是1995年秋天我在魯院上培訓(xùn)班的時(shí)候���,聽說王蒙要來上課��,我冒然提筆給她寫信����,跟她要一本簽名作品����,是王蒙主編的一套叢書,其中有她一本�����。沒想到一個(gè)星期后����,我就收到了她親自寄來的書�,并如愿以償讓王蒙在這本書上也簽了名��。
按說這是一本非常有紀(jì)念意義的書�����,我應(yīng)該好好珍藏才是����,可是由于二十多年里我數(shù)次變換住地,流離凌亂中����,我把這本書弄丟了。
口說無憑。在當(dāng)下這個(gè)時(shí)時(shí)處處充滿懷疑的年代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即使我把這事說出來了,又有誰信呢��?恰如范小青在《滅籍記》創(chuàng)作談中所說�����,“你信無可信���,你甚至連這個(gè)世界是真是假也無從確定了。
2
其實(shí)讀不讀《滅籍記》,我們都知道��,身份之于我們的重要性。之前出行必須隨身攜帶一張蓋著村居���、公社或企事業(yè)單位的介紹信,之后是量身定制的身份證�����。身份證歷經(jīng)一代的�����、二代的、防偽的�����、指紋的���,發(fā)展至今��,出示身份證的同時(shí)���,還要面對(duì)攝像頭刷一次臉……
我必須坦率地說����,《滅籍記》是范小青近十年創(chuàng)作的作品中最走心的一部,是最讓我掩卷之后久久不能釋懷的一部�。閱讀過程中�,我多次笑出了聲。通篇延續(xù)著范小青一貫的創(chuàng)作風(fēng)格,不管主題是否宏大���,不管故事是否沉重����,文字一如既往地輕盈、活潑、詼諧��、智慧、哲思,簡直就是文字版的郭德綱����。評(píng)論家汪政說����,《滅籍記》是范小青小說喜劇美學(xué)的集大成����。如此一部作品���,讓你怎么能不喜歡?怎么能不一笑再笑�?
然而,可是��,之后呢���?
毫無疑問�����,《滅籍記》絕不是讓你笑笑那么簡單。
評(píng)論家謝有順在《作家是創(chuàng)造精神景觀的人》一文中說,中國小說的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���,多是關(guān)乎社會(huì)�、國家�����、民族����、歷史的����,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題,也不太思索個(gè)體人生的困境或個(gè)體精神所遇到的難題����。
我想《滅籍記》正是這樣一部作品��。同樣是寫普通人、普通事����,卻飽含著先知先覺的哲學(xué)追問�。在無處可逃的社會(huì)洪流中�����,個(gè)體的命運(yùn)永遠(yuǎn)如隨波逐流的浮萍��,或許連浮萍都不是。
3
讀完《滅籍記》,我蠢蠢欲動(dòng)卻遲遲動(dòng)不了筆���。一方面是“近鄉(xiāng)情更怯”的欲說還休;一方面緣于《滅籍記》的作者是范小青�,是我無比敬重的前輩師長��,怕無意中冒犯她�。
寫這篇文章前,剛剛讀了《當(dāng)代文藝》推出的德國漢學(xué)家顧彬的訪談�����,他認(rèn)為中國當(dāng)代小說就是通俗文學(xué)���。之前他還有一句非常極端的評(píng)價(jià)��,說中國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就是垃圾�����。他的言論在文學(xué)界引起怎樣的反響���,這不是我關(guān)心的?��?陀^公正地講����,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肯定有其值得批判的��、惡俗的、丑陋的���、諂媚的��、垃圾的一面,但不能因?yàn)槿绱?��,我們就以偏概全��,就妄自菲薄���,就忽略任何事物都有其兩極性的定理。亨利·大衛(wèi)·梭羅有一句名言���,一棵樹只有長到它想長的高度后��,它才知道怎樣的空氣適合它�����。文學(xué)作品也是如此��,時(shí)間和讀者就是決定它高度的空氣��。
許多當(dāng)代知名作家���,如閻連科����、莫言��、余華�、格非、方方�����、遲子建�、魯敏、葉彌�、趙本夫、葉兆言����、蘇童、畢飛宇等�����,他們的作品是否通俗且不論,你能說他們的作品全是垃圾嗎����?就是我身邊的一些并不著名的80后、90后年輕作家們寫出的作品�,同樣充滿人性的光輝和神性的預(yù)言。單單以藝術(shù)價(jià)值的評(píng)判標(biāo)準(zhǔn)來衡量���,也不能全盤否定我們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的創(chuàng)作價(jià)值和成就。
用一句頗時(shí)髦的外交辭令套曰:這本身就是一個(gè)偽命題��。
作家畢飛宇說�����,我們不缺才華�,但我們?nèi)鼻閼选?/span>
這情懷就是你對(duì)生活對(duì)世界的態(tài)度,更涵蓋了你的價(jià)值觀��。
迷茫���、混亂�、虛空��,這是物質(zhì)豐富之后,人類精神世界必然要經(jīng)歷的陣痛�,對(duì)優(yōu)秀創(chuàng)作者而言卻是巨大的機(jī)遇和挑戰(zhàn)。你作品能否存活�����?能否長壽�����?能否經(jīng)得住時(shí)間和讀者考驗(yàn)�����?一定取決于你賦予作品的情懷和價(jià)值判斷�����。而《滅籍記》之所以贏得廣泛認(rèn)可�、共鳴,就在于它能叩擊到我們靈魂幽暗和社會(huì)痛點(diǎn)的這種情懷和價(jià)值判斷����。
4
這里我要把《滅籍記》的內(nèi)容重復(fù)一下,便于沒讀過這部作品的人��,更有可能理解我真實(shí)的表達(dá)。
本書講述了名字叫吳正好的主人公����,替父親尋找親身父母,最終引出一段特殊的歷史以及葉蘭鄉(xiāng)���、鄭見桃����、鄭永梅等一系列人物在這段歷史中的離奇境遇��。故事的主角是“籍”��,一張簡單的紙���,卻是契約,是證明���,是身份的象征���,是一張無處不在的命運(yùn)之網(wǎng)。
故事是荒誕的�,卻真實(shí)發(fā)生著���;人物是虛構(gòu)的,卻是我們無比熟悉的父輩曾經(jīng)����。作家以女性的簡約細(xì)膩、敏感尖銳和深刻內(nèi)斂���,寫盡了幾代人的命運(yùn)淵藪��,展示了作家對(duì)待過往歷史的審慎態(tài)度和個(gè)體反思�����。
范小青多次自謙地說��,她的作品和她的名字一樣����,又小又輕(諧音“青”)�����。也有評(píng)論家說過,范小青的作品總是少了那么“一口氣”����。我不知道這“一口氣”具體是指什么,也許就是作品的厚重度�����,而這厚重度又是什么���?中國作協(xié)副主席閻晶明如是評(píng)價(jià)說���,《滅籍記》是范小青創(chuàng)作歷程中具有標(biāo)志性一部作品,她在更高的層面以及更深的主題意義上找到了自己想要表達(dá)的東西。
我想這種表達(dá)就是那“一口氣”�,就是超越現(xiàn)實(shí)的對(duì)人性的終極追問和對(duì)世界的悲憫情懷。
5
每個(gè)人活著����,必須要通過種種“籍”來證明:我們活著�����,我們是我們�����。如果沒了這些“籍”,你就不是你�����,你媽就不是你媽����。也許有人相信你就是你,你媽就是你媽��,但為了證明這“相信”�����,你還得必須拿出“籍”來證明����。就比如我們現(xiàn)在拿著自己的身份證,還得面對(duì)攝像頭端端正正刷一次臉一樣�����。
說真心的����,每次這樣刷臉時(shí)����,我都會(huì)生出莫名地恐懼?���,F(xiàn)在整容術(shù)如此先進(jìn),換臉的普遍性指日可待���,我們以后又拿什么來證明這張臉就是我們自己的臉呢�?
這里����,我再說一個(gè)也許和《滅籍記》無關(guān)的話題。我父母都健在�,他們今年都八十出頭了,如果運(yùn)氣好����,他們也許能活到100歲。但是���,很遺憾的是,他們今年必須馬上要從他們生活了60多年的祖宅上搬走。故土難離��,父母很傷心����,他們甚至想早點(diǎn)死,這是人之常情�。但可以確信的是,從他們被動(dòng)搬離那一天起���,附屬于他們身份的情感和精神的“籍”����,就永遠(yuǎn)消失了���。
6
“一張‘紙’的存在與虛無����,‘身份’中的不可承受之重���,歷史中的隱痛和深憂����,遍藏不遇的往事與鄉(xiāng)愁……”
——這是《滅籍記》封面上的介紹。這本書究竟寫了什么���?究竟能讓你有何體悟���?它的文本價(jià)值究竟是什么?仁者見仁智者見智�,一千個(gè)讀者就有一個(gè)哈姆雷特,你不是我�,我不是你,你怎么能了解我�,我又怎么能代替你?
“我生本無鄉(xiāng)����,心安是歸處”。讀完《滅籍記》后��,我本能地想到白居易《初出城留別》這首詩中的句子���,一念再念����。
不想表達(dá)什么�,也不想討論什么��,建議沒讀過《滅籍記》的你,不妨讀一讀吧���!